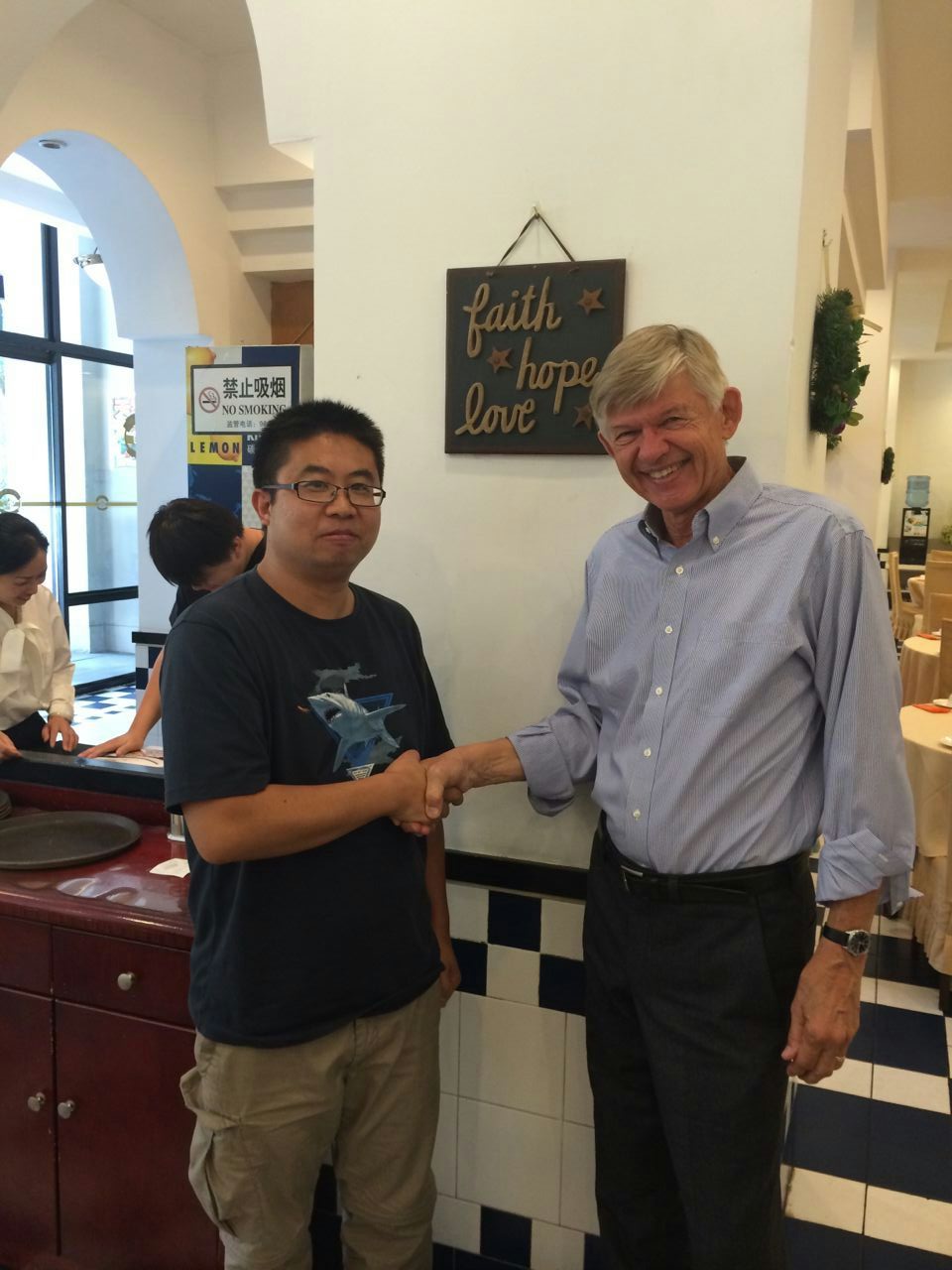今年我的工作重心之一,是校史馆和语言博物馆的筹建工作。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,20多年前,初到校园后的一幕幕场景不禁浮现在眼前。
完成报到工作,拿到新发的被褥、搪瓷餐具、校徽后,我惊奇地发现,我的学号竟然正好是96666,连着4个“6”!第一堂英语精读课上,老师推门而入,我一怔,她就是几个月前我的英语口试的主考官吗!
在筹建校史馆的工作中,一位学生助理问起现在行政楼边的建筑物是哪里,我脱口而出,那是牛津中心,那也是我在上外四年本科岁月里,最让我怀念的地方。后来要找牛津中心的照片,我翻来找去只找到一张在它门口樱花树下的独照。只能任由思绪带我重游一番当年的心仪之地。
牛津中心全称叫牛津中心阅览室。记忆中,它位于今天行政楼的南侧,如今已经改建成了绿地。整体建筑是东西向的平房,门口朝东。西墙外有做小土堆,土堆上建有凉亭。四周草木葱茏,绿树掩映,尤其是门口的两株樱花树,每当孟春之际,花吹雪的季节,也是校园内的一番胜景,常引得师生驻足。推门而入,左侧是宽大的阅览桌,右侧是一排排书架。
我的中学时代,学校图书馆馆藏量小,没有几本书可读。到了上外,图书馆当时还是用卡片查书,颇为不便。而牛津中心藏书量算不上多,都是开架的,只要进了阅览室,拿上代书牌,就可以随便浏览,但是不能出借。那里的书以英文为主,但又不限于英文,还有其他语种的书,而且内容不限于语言学、文学。我在勘察完地形后,便如饥似渴地投入牛津中心的怀抱。至今,我还保留着当年的读书笔记:有圣经地理学上描摹下来的地图和考古分期表;有西方哲学史上寻来的金句;还有从一本1840年代英国出版的希腊语教科书上觅来的希腊语读音规则……要是没记错,在最靠西墙的书架上,还陈列着几排盲文书。我当年还取下来,闭着眼“抚读”过。
喜欢牛津中心的理由,除了藏书恰好适合我口味之外,那里的读者人数不多不少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。人太少,显得太冷清,我还没有修炼到太上忘情的阶段;人太多,容易心烦意乱,再多一点就要预先占座了。记忆中,来牛津中心里看书的人,除了考试周前,差不多每张桌子上就一俩个人,显得不温不火,清净而又不失温暖。唯一遗憾的是,若干年后,得知朱磊兄也爱去牛津中心看书,未能提早几年相识也是人生一大憾事。
我的学问像个杂货铺,一半是少时从电台、电视里的《星期日广播英语》、《Alles Gute》、《Espero》之类节目里蹭来的,另一半是牛津中心给我的。今年的暑假,我们的东方语学院资料室终于改头换面变成了文献中心。我也努力把它打造成像牛津中心那样的阅览室,不大不小,有温度却不炽烫,书不算多却足够读,能够触摸到历史,能够和知己喝喝学术咖啡……没有华丽与喧闹,只有静谧和朴素。
(民盟上外委员会盟员、东方语学院信息资料室主任 李卫峰)